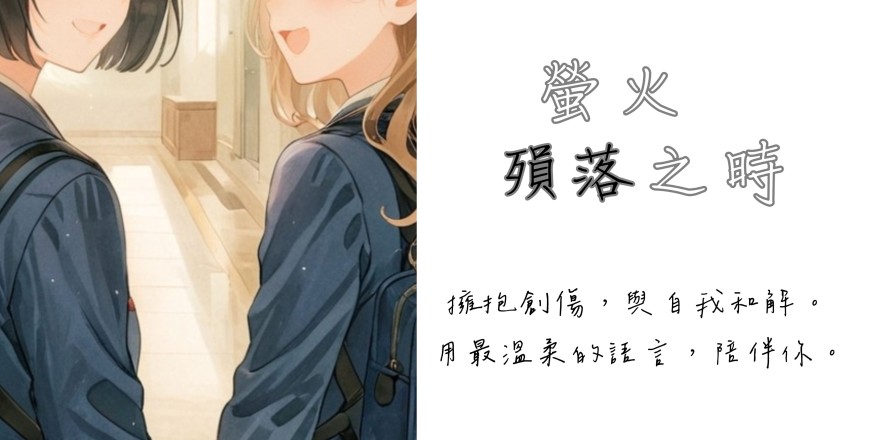謝謝你願意讀到這裡。真的,很不容易呢。
從三個月前開始構思劇情,到現在第二卷終於劃下句點……自從進入昀彤線,每寫完一章我都哭得不像樣。謝謝昕柔,也謝謝昀彤。我真的,好愛她們。
這一卷從昕柔的英文作文主線出發,延伸出對「自我價值」的反思與探索。那種從他人期待中堆積而來的壓力,甚至讓人懷疑:是不是只有夠爛,別人才不會失望?最後,昀彤一句簡單的話點醒了我們──一件事的價值,不在於別人期不期待,而在於「我自己喜不喜歡」去做,過程中有沒有真心享受。關於自我價值的探索還能延伸很多主題,這部分希望之後第三卷開始,她們能一步步繼續發現更多可能的答案。
接著,從第二十三章開始,就是昀彤主線的開場了!
這一段我偷偷埋了很多心理學概念(笑),也許有些地方比較燒腦,如果不小心頭昏可以跳過沒關係!畢竟,這也可能只是我自己對自身經驗的解釋,也有可能會有錯誤。
這裡想先介紹一個工具──內在家族系統(IFS)。IFS將內在心理結構分成「管理員」、「救火員」,以及「被放逐者」。我習慣把前兩者統稱為「守衛者」:像是昕柔內心那位總是在受傷後挺身而出的「大人」,會第一時間保護自己,或在危機中採取行動。而「被放逐者」,我稱之為「內在受傷的小孩」,是那個長期被忽視、被遺忘的部分──就像第二十九章〈未完成譜曲〉中出現的「小小昀彤」。你有沒有發現?昕柔的內在形象,是成熟的大人;而昀彤的,卻是一個小孩。這是因為她們受傷的年紀不同。
昕柔在國中時受到朋友的傷害,當時的「自我」已經有一定成熟度,因此發展出「過早出現的父母」角色來保護內心。反觀昀彤,她的傷口來自更早的童年──她從小就被灌輸「妳就是不夠好」的信念。這使得她從一開始就強迫自己堅強、不能脆弱,久而久之,她整個人就變成了「守衛者」本身。那個真正受傷的孩子,被藏得太深太深,深到連她自己都忘了她的存在。
我相信,第二十五章〈好像一切都沒有意義〉,大概是這一卷最鋒利、最讓人難以承受的一章。
為什麼那一章「斷」得那麼徹底?因為信念徹底崩解了。昀彤深信的信念是:「因為我不夠好,所以我必須更努力。如果不努力,大家(父母)就不會愛我。」但她突然發現:「原來我不管怎麼努力,都沒有意義。我永遠不會被接納。」在第二十六與二十七章的家政課事件中,她像斷線的木偶,情緒全然遲鈍──不是她不痛,而是「太痛」了。傷害來得太猛太快,就像突如其來的高壓電流,如果不立刻阻斷,「我」會被電死。所以守衛者出手了:剪掉線路。於是,整個情緒系統當機。
然而,在第二十七章裡,她看到昕柔「因為她而哭泣」,那一刻,有人看見了她的痛,她才終於感覺到:「啊,原來這真的……很痛。」後來她開始覺得自己只是「想要」昕柔,於是感到恐懼。有些人可能會以為那是「佔有慾」,但我想說,其實那是「依附渴望」──是對「無條件的愛與接納」的渴望。
昀彤的原生家庭讓她缺乏這種愛,因此學會了扭曲的自我認知、建立起不安全的依附模式。她在這樣的成長歷程中,被一條條「認知枷鎖」套住,那些枷鎖就是她「活著的方式」。而昕柔的出現,是一種「挑戰」。挑戰那些認知、那些活法。所以她害怕。她怕自己無法承受「真正被愛」之後的變化,怕自己會崩壞。昕柔,就像那個她從未擁有過的「溫柔的接納」本身。當這樣的愛真的出現在面前時,她本能地想逃跑。
在依附理論中,有所謂的安全依附、逃避型依附、焦慮型依附等。這邊就先不多展開,但昀彤顯然偏向逃避型。她內在的小孩突然冒出來,想說的是:「我太差勁了,還是逃吧……別讓她看到。」如同第三十三章昕柔說的──守衛者出現,有時不是為了保護我們不被傷害,而是因為我們覺得自己爛透了,不值得被愛。
最後,說說那首歌,《螢火》。這首歌創作完成時,我自己也很感動,大概是我聽了多少次就代表昀彤聽了多少次吧。昕柔,是我最貼近的角色之一。我看著她從那個總是小心翼翼、躲在玻璃牆後的自己,一步步與內在的守衛者對話、和解,然後,學會把自己的溫柔遞出去。真的,那一刻光是「感動」兩個字,已經說不清了。
昕柔,妳真的很努力了呢。(摸頭)
這首歌,其實結合了我之前創作的兩首舊作:《憶海殞沙》和《想變得普通》──前者代表昕柔,後者則是昀彤。這次,《螢火》則是從「未命名譜曲」一步步蛻變而來。它在第三卷中還會繼續出現,甚至會產生變化,拭目以待。
謝謝你願意陪著她們,一路走到這裡。
如果你願意繼續陪她們一起走下去,我也會在這裡,牽著她們的手,繼續把她們的故事說完。
15Please respect copyright.PENANAVb3eDBnAcu
2025.07.12 千夏
螢火,歡迎試聽。
15Please respect copyright.PENANA7PTBZG88i8
15Please respect copyright.PENANAmikscxXFRP